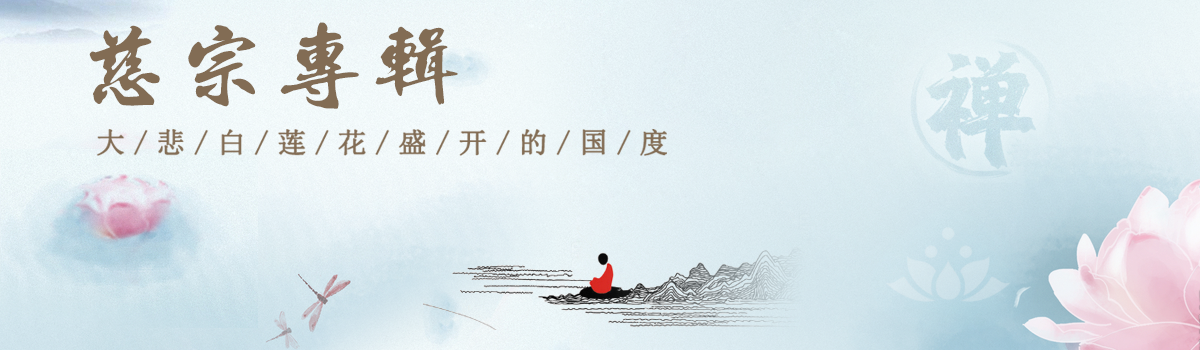
太虚:普度众生之宏愿
——普通民众、知识分子
马海燕
今天所谓的“知识分子”,在古代则是“士大夫”,吴晗先生认为:“官僚、士大夫、绅士、知识分子,这四者实在是一个东西,虽然在不同的场合,同一个人可能又几种身份,然而,在本质上到底还是一个……平常,我们讲到士大夫的时候,常常就会联想到现代的‘知识分子’。这就是说,士大夫和知识分子,两者间必然有密切的关联。官僚就是士大夫在官位时的称号,绅士是士大夫的社会身份。”[1]士大夫的知识,当然是以儒家之学为主,因为儒家思想作为中国古代社会的统治思想、精神支柱,这是不可否认的。
尽管佛教在中国经历了长久的发展,并且融入了中国文化之中,唐代时期曾达于鼎盛,诸宗并起,人才辈出,一时号称显学,特别是慧能创立的禅宗,俨然成为中国佛教之代名词,一直以来都深得士大夫们的喜爱,但喜欢归喜欢,主流士大夫们对佛教的态度依然十分明朗,他们从来没有停止过对佛教的批判,历史上反佛的著名人物有傅奕、韩愈、程子、朱子、颜元等。韩愈有《谏迎佛骨表》,以华夷、忠孝等语,诟病佛教;程朱虽然自称“出入佛老数十年”,但仍然处处贬低佛教。即便是处于时代大变革的明末清初时期,士大夫中虽然多有选择逃禅者,但他们对佛教的态度依然是若即若离的,如隆武时著名的吴钟峦,曾作《十愿斋说》,其中谈到“吾愿子孙世为僧,不愿其登科”,但又说:“吾愿其读圣贤书,不愿其乞灵于西竺之三车”。[2]黄宗羲胞弟黄宗会,他反对遗民作和尚,他说:“不为异姓之臣,而甘为异姓之子乎?”[3]士大夫对佛教的排斥依然不改。
由于士大夫对佛学抱有极深的成见,佛门中人也对士大夫的佛学修为深表怀疑,苏东坡可以说是士大夫的代表人物,一生以好禅闻名,明末曹洞大师永觉元贤则认为:“东坡以禅自负,人亦以禅归东坡。渠虽有悟入,而死于东林印下,不能彻证,依旧只堕在聪明境界中,何能敌得生死?至其晚年,乃好长生之术,用冬至日闭关养气,卒以此得病而终,禅也其若是乎?禅也其若是乎?”[4]现代新儒家的宗师熊十力先生则批评古代的士大夫是“所资于禅者,每得其似而遗其真。”[5]由上可见,士大夫阶层与佛教界人士之间始终有着一层隔阂。
时代发展到了清末民国,西学随着帝国主义用坚船利炮撬开的大门蜂拥而入,有直接从欧洲、美国输入的西学,也有转道日本间接传入中国的西学,不管如何,其输入的深度和广度是空前的。与汉时佛教文化的输入不同,西学的强大攻势令士大夫(知识分子)们忧心忡忡,中国文化面临巨大的危机,学界之情形为之丕变,他们纷纷把目光投向了已经与中华文化血溶于水的佛学:“晚清的大变局中,之所以会出现佛学的复兴,也就是近代中国人在理解西方知识与思想时,需要一种可以帮助自己理解西方的资源……于是不仅有了理解和解释的依据,而且有了接受和消化的自信,晚清佛学就这样兴盛起来,就这样改变了人们对西学的理解,同时也就这样改变了人们对佛学的理解。”[6]这里的“人们”其实更多的还是指士大夫阶层。这一时期,佛学受到了主流知识分子的认可,他们深入研习佛学,其中也不乏信仰者,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康有为、谭嗣同、杨文会等。
对于知识分子表现出的参与佛学研究、推动佛学普及运动的热情,太虚大师感到非常的振奋,他曾说:“至近来渐有之佛学社等,得一般士夫之共同研究,渐能将佛法流通于世。由是以观,佛法似有发达的希望,以对不振作之僧伽日趋衰落,适成一反比例。盖旧时之读书人读孔、孟之书,了知事亲以孝,亲君以忠,乃至事神以敬等,而于佛法则鲜能研究了解及之;因之,信仰佛教者,皆属不读书之农、工、商与妇孺,只知崇拜以祈福、消灾、延生、度亡等,致今日渐被世人诟为迷信!所以致此之由,盖有许多的因缘,识者类能道及,慈不赘说。近来读书人的思想业已开放,对于佛教已渐能自由探讨,由研究以至于流通,遂引入不少知识份子的信仰,于是佛法于社会便日见昌明矣!”[7]太虚大师认为,古代的士大夫也就是知识分子因为执守孔孟之道,于佛法少有人愿意研究和了解,从而导致古代信仰佛教的群体多是那些不读书的底层民众,佛教还因而被人诟病为“迷信”,现在有了大批知识分子加入了佛学研究甚至信仰佛教的队伍,中国佛教就有了振兴的希望。
太虚大师因为知识分子的重视佛学而对中国佛教的发展充满希望,他就此提倡“人生佛教”。“人生佛教”涵盖之范围很广,其完整内容包括以下四个方面:
“一、人间改善。以佛教五乘共法中之五戒等善法净化人间。从家庭伦常,社会经济、教育、法律、政治乃至国际之正义公法,若各能本佛法之精神以从事,则均可臻于至善,减少人生之缺憾与痛苦。故现实人生可依佛法而改善净化之也。此虽一般科学、哲学及儒家等学术之所共,而佛教亦有详明发挥与其不共之特质者在;本此特质,进以融摄科、哲、儒学等所长,则佛教对此改善人生之目的,自可发挥其无尽之效力也。
二、后世胜进。生命乃无穷尽之长流,循业力以受报,生死死生,此界他趣,轮回无已;故不惟图现生之改善,且应进求后世之胜进也。修十善业及诸禅定、可获上生天界,持佛号、仗他力、可往生他方清净佛土;虽生死未了,而可得胜进优美之依正二报,免四趣苦,且可超出人道之上。是依佛法可达之目的与效果也。此在净土及密法,亦所注重;而世间之高等宗教,如耶教之求生天国等,皆同有此种目的。
三、生死解脱。后世胜进非不善;然诸行无常,有漏皆苦,生而不能不死,住而不能不灭,终不澈底。然则如何可断苦本而灭诸漏耶?生必死则求离于生,住必灭则诸有不住;截生死流,拔度苦海,而登涅槃寂灭之彼岸;我生已尽,梵行已立,所作已办,不受后有,生死魔军其奈何哉!是佛法又进一层之出世目的,乃三乘行者共达之效果,而为世间一般教学所不逮。
四、法界圆明。涅槃解脱、美则美矣,然尚不尽诸习气,不断所知障,不得一切智,于一切法界犹不能圆明。且一切有情皆我无始来之六亲眷属,奈何自求寂灭而不之或问耶?是故菩萨摩诃萨,摄一切众生为己体,痛等切肤,大悲充溢而度尽为誓。历经时劫,广求无边福智,尽断二障习气,终乃圆明法界而融遍无碍矣。是大乘至极之效果,亦佛法究竟之目的也。”[8]
这四者的关系是:“然以言终极,惟法界圆明之佛果始为究竟,亦可谓此乃全部佛教之真正目的;前三层皆为达此之方便也。”[9]我们不妨这么说,“人生佛教”的第一个方面注重佛教的社会意义,这方面是知识分子的特长,需要知识分子积极参与;第二、第三个方面则注重佛教的信仰;前三方面都只是佛教的方便之说;第四个方面才是佛教的究竟之说。
需要说明的是,太虚大师并不认为“只知崇拜以祈福、消灾、延生、度亡等”即是迷信,他也没有因此贬低来自不读书之农、工、商与妇孺的佛教信徒,因为这所谓的“迷信”,是以往对佛教缺乏同情与了解的社会舆论所造成的,是他人的“诟病”而已,他仍然把这些纳入“人生佛教”(即第二个方面);同样,知识分子所擅长、所热衷的社会事业、学术研究等,可以归于“人生佛教”之第一个方面,但与第二个方面都是方便之说,并无高下之分。
总之,太虚大师提倡的“人生佛教”乃是一个完整的体系,关注的是人生的诸多问题,其最终的归向乃是树立佛教的人生观,通过追求人格的圆满,最后解脱成佛。其参与者是广泛的联盟,既有下层之普通民众,也有知识分子,他的慈心是如此的广大,希冀借此以实现其“普度众生”的宏愿!
(作者已发文章,转载请注明出处,严禁剽窃。)
本文摘自马海燕11-3-24新浪博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