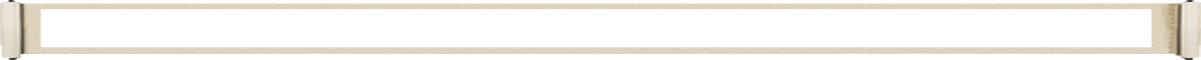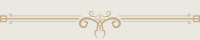
栏目导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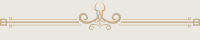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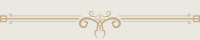
推荐文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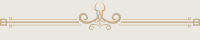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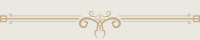
热门文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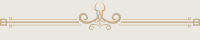
王袍僧衣一休梦之第一章佛法无边和第二章伤别离
作者:释楞严 文章来源:本站原创 点击数: 更新时间:2012-02-10 11:18:00
本文来源:悲华论坛 曾点击次数:1125 跟贴数:6
王袍僧衣一休梦之第一章佛法无边(1-3)
作者:付良举 日期:2004-03-30
导读:
一休禅师(1394-1481)
一休宗纯,法号一休,讳宗纯,曾自称狂云子、梦闺、瞎驴等。明徳5年(1394)元旦,一休出生。幼时名为“千菊丸(せんぎくまる。6岁进入安国寺,赋名为“周建(しゅうけん)”。安国寺里有很多良家的子弟,不能表明自己身份的周建吃了很多苦头,逐渐的才发挥了自己的才能。他住在寺庙的书库里,读通了许多经典著作。就是因为这一段插曲,他后来成为了“聪明的一休(とんちの一休)”被后世所传诵。1471年,一休78岁时,遇到了一位旅艺人——盲女“森(しん)”,于是彼此深深相爱。森照顾了一休大约10年,在这期间,他完成了汉诗集《狂雲集》。他写过许多情诗,袒露自己的爱情生活。在题为《梦闺夜话》的诗中,这样写道:“有时江海有时山,世外道人名利间。夜夜鸳鸯禅榻被,风流私语一身闲”。
一休被视为“疯狂”的缘由之一,也就在于他无视禅宗禁欲的戒律。他公开声称自己“淫酒淫色亦淫诗”,但是,他又没有象法然和亲鸾那样,积极进行宗教改革,创立新教派,公开否定禁欲主义。他无力挽救禅宗的颓风,只好以似乎疯狂的行动,以袒露自己的情欲来反对禅宗伪善的禁欲。
文明13年(1481年),大德寺重建工程大体竣工。11月21日卯时,操劳过度的一休禅师在森和几个弟子的看护下病逝,享年88岁。
一休禅师最后的遗言是:
『朦々淡々として六十年、末期の糞をさらして梵天に捧ぐ。借用申す昨日昨日、返済申す今日今日。借りおきし五つのもの(地水火風空の五大)を四つ(地水火風)返し、本来空に、いまぞもとづく』
在我生命中的每一天,在星辰闪烁的夜晚,我都会梦见佛光四射,大地安康,所有原本属于我的臣民高呼着我的名字,叫喊着,殿下,回来吧,我们需要您。而后,我会看到我的父王缓缓走来,抚摩我的额头,轻声说,孩子,你终于回来了,这个国度需要你!
这时,我就会醒来,遥望沉沉而辽阔的天空,泪流满面。
一、佛法无边
我习惯站在安国寺外的山顶之上,在寂静无声中看旷野无边,看日出日没,看花开花谢,每天修行完毕,我都会一个人来到这里,听着寺里悠扬而且醇厚的钟声,自己的心也会随之起伏跌荡,我的师傅,一个面貌苍老但却谦逊可爱的老人,很多时候,他会悄悄地走来站在我的身后,我们默不出声,也只有在很长时间之后,在他要回寺庙里的时候,才会对我说,周建,你今生注定与佛有缘。
每当师傅说这样话的时候,我的心都会加速,颤抖着,而后,流下几行淡淡的眼泪。
我是周健,京都安国寺里最为年轻的和尚,在我六岁那年,当自己才能够体会人间苦乐,在别的孩子享受父母疼爱的时候,我被送到安国寺出家。我从小都不知道自己的父亲是谁,我的母亲并没有告诉我,而奶娘玉江也没有说,只是殿下、殿下的称呼我,照顾我。那时我很快乐,虽然没有父亲的陪伴,但是,依旧在幸福中荡漾。
冬天,京都郊外苍茫雪地里的奔跑,伴随着玉江急促地追赶,并且疾声呼喊:殿下,殿下,千菊丸殿下,等等我,母亲温柔地微笑着注视着我们,以及不断倒地的黑衣武士,他们手中的战刀发出明亮刺眼的光芒……,所有情节都构成了自己对六岁以前时光最为深刻的记忆,这种记忆总会在以后的日子不断出现,从甜蜜变成痛苦,进而成为令人恐惧的梦魇,并且挥之不去。当我挣扎着醒来,在昏暗的烛光里,总会看见师傅那张慈祥而且温暖的面容,他会缓慢地用略感粗糙的手掌抚摩我的额头,苍白细长的胡须拂过我的脸庞,让我觉得安定,师傅会安慰我说,睡吧,周健,过去的已经成为历史,而人注定必须在经受磨难中长大。所以,在现在,当我长大了,也已经知晓了自己的父亲是谁,但却早已没有了童年那种迫切的渴望,与纯真的愉悦。
童年离我越来越远,童年的记忆在佛与师傅的教诲下逐渐淡化,我曾问师傅,如何才能忘记痛苦?
周健,痛苦缘于内心,当你不再去想,便不再感觉痛苦,师傅说,双眼放射出智慧而又深邃的目光,可惜我并没有读懂。我想师傅注定与佛相近,而不是自己。
师傅名叫像外法师,我猜想师傅的法名应该出于“万象之外”之意,刚入安国寺的时候,是师傅亲自为我剃度,并赐我法名周建。当我的头发一丝丝飘落,如风中的柳絮般飞扬时,我发现我的母亲激动不已,并且伴随着轻微的抽泣,我听见玉江轻声说着:殿下,殿下……
那时候我的年纪太小,并不明白皈依佛门即要尘缘全了,而现在,当自己对佛法有所通晓,对于母亲的思念,对于儿时那陈旧院落,漫天飞扬的大雪,对于屋外樱花绽放,玉江轻声呼唤的思念,却如同泉涌,无法抑制。
我记得我的母亲总喜欢叫我的乳名千菊丸,并且会拉住我幼小的手,教我如何用纤细的稻草编制出很多复杂但却美丽的饰物,我记得自己总会在满足中欢笑,那时,我同样是个平常而且天真的孩子。玉江总喜欢拥抱住我,亲吻着我的额头说,殿下,您是我们国家的希望,然后,她的眼泪会用同样的姿势滑落,落到我的嘴唇,温暖却有些淡淡的咸味。
我曾以为幸福会永远,我曾以为自己的童年会与别人一样,湮没在欢笑之中,虽然没有父亲,但自己却同时拥有母亲与玉江的爱,我同样是简单而且快乐的。直到六岁那年的冬天,一批黑衣武士闯入我们的院落,将我童年的幸福击撞地粉碎。
庭院的门大开,我躲在屋子里,玉江抱紧我,我能感觉到她身体的颤抖,冰冷的透彻,玉江哀求黑衣武士们放过我,我听见她口中说出足利将军的名字,但我并不知道他是何人,我的母亲站在屋子的门口,神情雍容而且高贵,寒风呼呼的咆哮,母亲鲜红的披风随风飘扬。
足利义满终究不想放过他?我的母亲问。
武士沉默无语,一个个冷酷得如同高山上最为坚硬的岩石。
如果想得到他,必定先杀了我。
母亲格外安静的表情让所有人感到吃惊,而我自己竟然在当时也没有发出一点哭声,只是握紧细小但却有力的拳头,无端记住足利义满的名字,现在回想,也许在那时,自己已经认定足利义满就是夺去自己童年幸福的罪魁祸首。如果没有皈依佛门,我至今还必定在尘世间游荡,在仇恨之中辗转反侧,生活成长,让仇恨的种子生根、发芽。
也许师傅说的对,痛苦缘于内心,当你不再去想,便不再感觉痛苦。
从六岁之后,从我来到安国寺之后,我注定是孤独而寂寞,所有的师兄都有一个温暖和睦的家庭,他们的父母会在每个月的最后一天来看他们,他们的父亲是高官、武士、富人……他们皈依佛门,为得只是求得一个法师的名分,而不是真正的世俗所迫,或者,甘心归佛。所以,每月的最后一天自己会更加孤独,无所遁形,只能隐藏于安国寺外的山上,看远处白云飘过,无比沉重的大雪封闭整座连绵的山脉,在旷野沉静中认真回忆母亲的笑容,玉江轻柔地呼喊,以及幻想我的父亲的影子。佛法要求忘记,而忘记却是无可奈何,希望总是让人宽慰的因子,不管信徒也好,凡人也罢。
站在安国寺外的山上,一遍又一遍沉浸于对童年往事的回忆之中,我记得六岁那年的冬天,当母亲与冷酷的黑衣武士对峙,我睁着或许恐惧但却清晰的眼眸注视,玉江冰凉的泪水打湿我的衣衫的时候,一辆马车突然破空而出,出现在庭院里,出现在所有人惊谔的视野里,马蹄腾空,一个头戴斗笠,衣着简朴的中年男子跳下马车,他跪拜着我的母亲,喊着夫人,并且如玉江那样,温柔地喊我殿下,从他满脸浓密的胡须之间,粗犷彪悍的脸上我看到一丝惊喜闪过。
中年男子缓慢地站起身,尔后,呐喊着冲向武士,开始奋力厮杀,鲜红的血液顺着混战人群锋利的战刀顶端缓缓流下,天空苍白而且辽远,大地逐渐成为红色点缀的绸缎。男人保护着我与母亲、玉江上了马车,向着京都的东南方向飞奔而去,疯狂的武士一个个倒下,但更多的依旧高举明亮的战刀紧追不舍。
鲜血不断倾洒,尸体一路横陈,这是我第一次面对死亡,虽然,我曾看到过农庄里因为饥饿而不断倒下濒临死亡的农夫,我曾触及过京都繁华大道上蹒跚前行面黄肌瘦的老人,而他的对面却是灯红酒绿富贵高歌的酒楼,但那些并不是因为自己所引发的死亡,我感到了真正的恐惧。
我小声问玉江,我们会被杀死吗?玉江抱紧我,坐在颠簸的马车里,强颜欢笑地轻声安慰我,当然不会,殿下,请别害怕,我们不会有事的。玉江拍打着我的身体,为我轻唱那首分外熟悉的歌曲,她拼命地微笑,表示轻松,但发抖的声音最终出卖了她,玉江掩面而哭。我的母亲则双目禁闭,紧缩着眉头,泪水从她的脸上无声滑落。
在一座高山的前面,马车停了下来,车外中年男子用他那沾满鲜血的双手卷起车帘,夫人,到了,他对我的母亲说,急促地呼吸,然后是大口大口地猛烈吐血。我下了马车,安静地望着男人的身体,他的衣服几乎被血染遍,不知道是谁的鲜血,我看见他身体上的伤口还在不断往外涌出鲜血,他跪在地上,亲吻我的额头,他指着面前的高山,从山上传来悠扬而且雄厚的钟声,温柔地对我说:殿下,我亲爱的殿下,山上就是您的归宿,请原谅我不能再保护您了,他冲我微笑,然后看着我的母亲,与玉江,粗犷冷峻的脸上落满雪花,他大声呼喊着,殿下,请您一定坚强地活下去,因为,您是我们整个国度的希望。殿下,请相信,佛法无边……
他死去的时候,钟声再次敲响,我发现,我的母亲泪如泉涌。
六岁,我来到安国寺之后,寺里寂寞的人就成为两个,像外法师与我,我相信无论何种原因所致,像外法师也是寂寞的,特别是在每月的最后一天,否则,那一天寺外山上的身影就不会出现两个。
师傅,您也寂寞,对吗?十二岁那年,我终于忍不住地轻声询问站在自己身后,已垂暮年苍老的师傅。
像外法师没有回答,许久之后,他缓声说:周健,寂寞分很多种,你说,我应该属于哪一种?
寺庙里传来无比繁华的喧闹声,那是师兄与家人团聚的欢乐表现,在佛法笼罩的地方,他们依旧没有摆脱世俗的侵蚀,我转过身,望着师傅的眼睛,说,精神!
像外法师沉默不语,但我却在他微笑的眼中发现了如同当年救我那名中年男子脸上同样的惊喜闪过。山上保持着相对的安静,绚烂的云朵布满天空,夏天到了,但傍晚的来临却不见得缓慢。
周健,你今生注定与佛有缘。法师转身离开。
也就是从那天傍晚,从我十二岁那年一个夏天的傍晚开始,师傅说,我今生注定与佛有缘。而我却隐约感到,今生,我也无法超脱尘世的羁绊。
因为,我无法做到彻底的尘缘了尽。我总想彻底地弄明白为什么自己要将一生交托于佛祖,与他面前长明不熄的香火,在烟雾缭绕的大殿里,与其他人一样,我们端坐着聆听像外法师的教诲,也就在那一刻,我才能短暂地忘记对世俗世界的思念与徘徊,离开后,却又浮想联翩。
我问法师,如何才能真正忘记?
该忘记的时候就会忘记,如同凤凰涅槃,勉强不会成功。
安国寺的时光平静但却急促,从六岁离开我的母亲到现在,不知不觉中,我已经在安国寺度过了十一年,冬夏交替的日子里,这十一年的光景如同溪水流淌,平静缺少波澜,如果记忆能够分离,除了六岁以前的片段,这十一年的记忆却是循环不变,只保留了冬天那飞雪弥漫的山顶,和法师苍老如一的面孔,以及他脸上如同波浪般日渐增多的皱纹,记忆中的波折点点滴滴,于我而言,稀少但却深刻,比如自己与足利义满的第一次见面。
那是一年的春天,万物复苏,大地充满着浓郁的生命气息,而我却失手打碎了足利将军珍藏在安国寺里名贵的瓷器,将军勃然大怒,他派人到寺里请法师去府上给他一个合理的解释,师傅有些忧郁,他喊我到面前,说,周建,佛祖安排,命运的车轮转动至此,与我一同去吧,该面对的迟早都要面对。
当时我并不明白师傅话语的涵义,只是有些莫名地激动,京都的繁华远比寺庙里苦修有吸引力,何况,我也想去亲眼见见,那个曾经指派武士,让我皈依佛门的将军。我没有丝毫的恐惧与胆怯,我想只要有法师的存在就会有佛的保佑。那时,我相信佛法无边。
我与法师步行前往足利将军的府邸,沿途满目萧条与凄凉,我不明白,在这个国家里,为什么繁华的旁边还有那么多食不裹腹的子民,路边的村落引起了自己对六岁之前时光的长久怀念。
将军的府邸富丽而且堂皇,门外的石雕狮子栩栩如生,让人望而生威,我发现所有从门前经过的人都会呈现出一种无比恭敬的神态,我的师傅却很安详,他说,周建,我们到了,进去后,将军如要问你,你就按佛的旨意去回答。
我用力点点头,一个衣着华丽的女子领着法师与我穿过威严的门楼,来到府邸的庭院内,院子里种满各种各样的树木花草,比安国寺外山顶繁盛,夏天时分,花草开放着千姿百态艳丽的花朵,使得整个院子香气怡人。
将军就在那边的屋子里等你们呢,美丽女子伸手指着一条走廊的尽头说,她的头发顺长而光滑,轻柔地垂下铺展,从她的身上散发出我曾熟悉的母亲一样的气味。
法师与我拾级而上,穿过走廊,来到了那间小屋的门外。
既然来了,就请进来吧,从小屋里传出低沉的声音。门打开,跳入眼帘的是屋子中央的方桌上供奉着的佛象,以及香烛闪烁,烟雾弥漫,一个有些苍老但却容貌威严的男子正座在佛像的旁边,我听见师傅恭敬地对他说着将军的字眼,我明白,这就是我生命中的夙敌,足利义满,他很高大,宽阔的肩膀上披着一件血红的长袍,他很虔诚地冲着师傅一拜,那种虔诚让人信以为真地感动。他盯着我,眉头紧锁,但很快又舒展开来,然后,他让我与法师落座。
将军,瓷器是我打碎的,要处罚就处罚我吧,师傅说。
法师,那瓷器非常名贵,不是处罚谁就能补救的。
可是,它已经碎了……
法师与足利将军全部沉默,将军反复滚动着他手中的檀木佛珠,伴随着佛珠的滚动,师傅的神情越来越凝重。
将军,所有的生命最终的归宿如何?我轻声问将军,气定神闲,将军狐疑地望着我,他无法明白,一个年少的小和尚竟然会大胆地向他提问。
有生就有灭,足利义满还是回答了。
那么,有形的东西呢?
最后亦是灭亡。
不分贵贱?
不分贵贱,都得灭亡。
那么,我微笑着望着将军,您的瓷器呢?
足利义满楞了一下,转眼之间他仰头大笑,好,好,你是周建?
是,我是周建。
安国寺的周建?
是,安国寺的周建。
好,周建,不错,不错,不愧是他的儿子。大笑之中的将军仿佛有些疯狂,我却看到一丝忧伤从他眼中闪过。
我与法师离开的时候,足利将军送我们到门外,他轻轻抚摩我的额头说,殿下,在寺庙里好好做你的和尚,今生你注定与佛有缘。我无法猜测到足利将军话语的含义,但是,当我回头去望法师的时候,我看到师傅在会心地冲我微笑,那种笑容连最明朗的天空也比不上。
与足利义满见面很久以后的一天,端坐在安国寺大殿里,我问师傅,为什么足利将军也会说我与佛有缘呢?为什么,他会放过我?
因为……周健,请相信佛法无边,法师悠长的声音如同来自另外一个国度,这时,寺庙里钟声响起,雄厚而且辽远。
这天,站在大殿的门外,我仰望着天空,每年,京都异常寒冷的冬季总会早早降临,而且持续的时间会很长,如同我所经历过的十七年的光阴,四季分明的特点在这里,夏天只成为匆匆一瞥的过客。安国寺里大雪纷纷,白雪皑皑,仿佛天边的白云一尘不染,我开始想象着京都郊外那个破旧的庭院里,母亲温暖的笑容,玉江粗糙但却温柔的双手抚摩我的额头,轻声叫着我,殿下,殿下,等等我……。
周建,在想什么?
回过头,我看到了站在大殿中央的师傅,这个陪伴我十一年,耐心教我诵经坐禅,吟诗赋词的老人,此刻,他正在慈祥微笑着望着我,他的胡须雪白的如同大殿外面零落的雪花,他的影子映在大殿里,狭长而硬朗,在他的身后,是被烛光灿烂衬托着的佛像,猛然间,我突然发现师傅已经苍老许多,如同自己的长大。
法师向前迈进几步,与我并排站立,雪好大啊,你看,周建,冬天已经来了,夏天还会远吗?生命同属自然,规律无法避免,不论长短,它都有存在的价值,不是吗?
我没有回答,只是如同寺外山顶之上平静的情形,我们站立着,不去说话,多年来的相处,已经让我习惯了与师傅之间地默默相守,只因为,我们就是安国寺里最为寂寞的一对。
师傅,我问,佛法必须寂寞才能完成吗?在自己一天一天长大,他却一天一天衰老的时候,当自己突然意识到寂寞真实存在的时候,我出声问我的师傅这样的问题。
寂寞是因为你曾融入过世俗,而现在却又离开,所以你会感到寂寞,而佛法就是在这种反复体会中才能感悟。法师缓慢地回答我,我忘记问他为何要如此循环,忘记问他这一切又是否值得?
周建,你来安国寺多久了?
法师缓慢地问我,仿佛在翻阅一本沉重而且年代久远,破旧不堪的佛经。
十一年了。
你已经十七岁了。
是的,师傅,我已经十七岁了。
你已经十七岁了,你已经……十七岁了……,法师自言自语着,然后迈着沉缓地步子走出大殿,大雪飘落一身,与他白色的胡须融会交织,他的身形有些蹒跚。法师蹒跚着朝寺门外走去,寺院里顿时变得空旷无人,白雪覆盖的大地上落下法师一个个清晰的脚印。我想,也许,他只是为了自己的老去而忧伤。
十七岁的年龄让人羡慕但却充满烦扰,倘若,我的母亲没有离开京都,而自己的出生也不是在偏僻的村落里;倘若,我的国度从未有过裂变纷争,倘若,足利义满甘于满足将军的权高位重,或许,我的轨迹就会发生扭转,而不是现在这样将自己十一年的光阴洒落在安国寺的每个角落。十七岁的年龄,让我已经能够分辨出什么是繁华似锦,什么是贫困交加,倘若,六岁以前,我的母亲为我编制出复杂但却美丽的饰物就能令自己开怀大笑,而十七年后,我却选择在梦境里,演示着自己曾经可能有过的生活。
法师离开我的那天夜晚,雪下的更大,纷纷扬扬,熟睡后我做了一个长久的梦,在梦境里,我来到了京都富丽堂皇的宫殿,我看到皇宫里灯火通明,那里的光亮远胜于安国寺大殿之上长明不熄的烛光,我看到一个服饰华丽,相貌俊朗但却有些威严的中年男子大笑着迎上我说,孩子,你终于回家了。宫殿里所有人都跪拜在地,双手高举,呼喊着,殿下,您终于回来了。在宫殿高耸的皇座上,坐着我泪流满面的母亲,她的身旁站立着微笑注视我的玉江,以及那个在我记忆中为保护自己而死去的中年男子,他粗旷的脸上滚动着晶莹透明的泪光。足利将军突然从宫殿的屏风里走出,单腿跪下,抬头望着我,无比真诚地说,殿下,欢迎您的回来,那种真诚让人心潮澎湃……
我又一次挣扎着从梦中惊醒,抹去额头少许的汗水,四周寂静地没有一丝生机,走出禅房,来到安国寺的庭院里,大雪依旧飞扬,在飞扬的雪中,我隐约看到一轮明月挂在空中。自从我的师傅在十二岁那个傍晚说我今生注定与佛有缘之后,不论每晚从何种梦境中惊醒,我就再也没有看见过师傅那张布满皱纹苍老温暖的脸,没有听到他的轻声安慰,周建,过去的已经成为历史,而人注定必须在苦难中经历成长。而自己的梦境也开始由原来反复出现的童年景象转变为对另一种身份的体验。
夜晚的安国寺是安静,但却孤独的,如同我自己,在山的顶端,与凡事相隔,与大地相远,与世俗无牵,佛门本应该是一个单纯而且无欲的境界,佛法的及至就是与世无争,彻底忘却所有尘缘往事。可惜,自己在经历了十一年的佛门修为后,非但没有将童年、将母亲,以及尘世中与自己有着千丝万缕关联的人忘记得干干净净,随之年龄的增加,对于自己另一种身份的向往——如果不是幻想的话,却愈演愈烈。反复出现在相同的梦境中的还有那个,从我出生就从未见过,是我父亲的男子,这个国度伟大但却无奈的天皇陛下。我不知道这究竟是谁的过错,难道十一年前安国寺的剃度只是让自己表面的身份得到改变,从而免去杀身之祸,还是我本天生资质愚钝,十二岁那年师傅对我说过的今生注定与佛有缘,仅仅只是个善意的欺骗?
来到安国寺,到现在,十一年的岁月里,我与自己朝思夜想的母亲仅仅见过一次面。
在我十五岁的夏天,我的母亲来到安国寺找寻我,短暂的谈话让我明白了自己身世的与众不同,让我清楚,在自己的血管里流淌着这个国度最为纯正的皇族血统,以及所有变化背后不为人知的原因。
那天,不是每月的最后一天,寺里寂静一片,我依旧独自站在山的顶端仰望天空,天气罕见稀少的晴朗,临近黄昏边缘,天边的云朵逐渐隐退,天空中盘旋着归巢的云雀,发出阵阵尖锐的鸣叫。
回过头,我看到了站立在一棵参天大树下面的母亲,还有玉江。
多年未见,我的母亲依旧高贵典雅,虽然身穿普通的服饰,但从她身上我依旧感觉得到那种熟悉的高高在上、不容侵犯的气息,母亲冲我安静地微笑,笑容里却有着莫名的忧伤。在她身边的玉江,嘴角翕动,仿佛是在喊着童年里相同的称呼,但我并没有听见。
大树参天,绿叶茂密,多年未见,朝思慕想的母亲就站在自己面前,注视着我。这种场景在夜晚的梦中曾出现过上百次,让我以为,现实之中自己就会不可抑制地冲过去,扑进她温暖的怀抱掩面痛哭,但那天我却没有,过分的冷静让自己感觉难过。
我与母亲相隔几丈,却仿佛几千米的距离,离别多年,人有了恍如隔世的感觉,我们相互注视着,沉默无语,天色逐渐暗淡,圆月挂上墨蓝的天幕,晚风习习,吹响母亲鲜红色的披风。
周建师傅,多年来你可好?许久,母亲缓声问我,但却不是对儿子的口气,淡淡地没有起伏。
我点点头,我只能选择点头,当梦想有一天真地能够实现,人并不一定就能坦然接受,佛法与师傅的教诲让我学会了克制。
殿下……,殿下,真的是您吗?殿下,母亲旁边的玉江终于哭泣着俯倒在地,黝黑的长发在月色的照射下呈现出华丽的银白。
母亲转过身对着俯到在地的玉江说,他已经不是殿下了,玉江,他……,母亲回头看着我,一字一句地说,他是周建师傅。
玉江抬起布满泪水的脸,清醒但却痛苦地说,是,夫人,我知道他不是殿下,是周建师傅,可是……夫人,您看,他已经长这么大了。夫人,您看,他多像我们的天皇陛下。玉江的脸上挂着会心的微笑,而我的母亲依旧不动神色。离别太久,一切都在变化,时世轮回,与身份无关。
那晚,我的母亲略带悲伤地对我说了很多,那晚,月光异常的绚丽明亮,所以,在母亲将要离开的时候,我才发现了从她眼角流下的液体,晶莹得反射出刺眼的光芒。
我只是偶尔地点头,不出声地站在她的对面聆听似乎与自己无关的故事,自始至终伴随着玉江的泪水,和阵阵来袭的夜风。
我的母亲告诉我,我的父亲就是这个国度最伟大的天皇陛下,他英明神武,英俊而且善良,他结束了国家长达半个世纪的混战,统一了整个国家。母亲告诉我,我的父王会为了人民的饥饿而让自己紧衣缩食,会为了国家的安定团结而自甘忍辱负重,我的母亲说起父王时,眼睛突然放射出一股浓烈怀念的神采,但转眼间恢复自然。我的母亲说,尽管她自己曾经历过繁华富丽,尽管在孕育我之时我还拥有殿下的称号,有着继承王位,成为国家未来王的机会,但这一切都被足利义满,这个曾经鼎立相助父亲统一国家,但却不甘心只做将军的人打碎。
他想替代你的父亲,成为国家的王,成为新的天皇陛下,如果自己不能够实现,他想让足利家族的一员替代你的位置,继承本该由你继承的王位。母亲的眼睛突然变得明亮,但很快暗淡无色,所以,我们只能逃离,离开宏伟的皇宫,隐藏在偏僻的村落,让你从出生就成为普通的人,而这一切,仅仅是为了保全你的性命,包括让你皈依佛门。
母亲说,告诉你,并不是想让你复仇,夺回原本属于你的王位,只是想让你明白,日后,成为你父王一般伟大的人,以佛的法力去感悟那些属于你的子民。因为,你已被佛祖垂青,因为,佛法无边。
佛法无边?
一时间,我仿佛看到了十一年前,在自己六岁那年为保护我而战死的中年男子亢奋的脸,他遥指着安国寺大声告诉我,佛法无边。仿佛看到足利将军轻轻抚摩我的额头,对我说,殿下,你已经被佛垂青。我迟疑地望着母亲,母亲的表情柔软温和,如同童年时看我的表情,满眼鼓励与赞赏的神色,我明白这背后包含的痛苦。
当母亲说要走的时候,玉江突然扑到我的脚下,抬起头,说着殿下,无论何时,你才是我心目中未来真正的王。然后,埋头哭泣,她的泪水洒湿我的衣襟。母亲没有阻止玉江的哭泣,她转过身,似乎想要离开,我看见了从她眼角轻轻滑下的泪滴,跌落在脚下的花朵上。
佛法无边,难道佛法真地无边?与母亲见面那天起,“佛法无边”的字眼如同生命的影子与我不舍不弃,十五岁的自己对佛的旨意只是似懂非懂,我不明白法师、母亲,以及那个曾为我死亡的中年男子,为何齐声嘱咐我相信佛法无边。
我陷入了迷惘的精神追寻,我不知道哪里才是真正属于自己的出口,我越发喜欢独自一人站在寺外山的顶端,冬天,然后夏天,然后又是冬天,……
转眼我已经十七岁,十五岁之后,喜欢孤独不再是逃避别人的团聚,而是自己需要选择。
十七岁的冬天,大雪弥漫,寒风咋起,我的僧袍在风中摇曳,呼呼做响。
站在风雪交加的山顶上,拥抱天地无际,这一刻,我忘记了世间一切纠缠,忘记了自己从前的身份,忘记了自己现在的法号,忘记了,佛法无边。
周建……
回过头,在那棵两年前母亲曾经站立过的参天大树下,站着我的师傅像外法师,他神情悠然地望着我,眼睛呈现出如同湖水般的平静无澜。
周建,你在想什么?
法师问我,很镇静的口气。
师傅,难道佛法真地无边?我突然鼓起勇气问起了这个隐匿在自己心中多年的问题,不由佩服自己的勇气,归依佛门,在佛祖麾下修行,竟然不相信他的无边,我明白,自己并不是一个合格的信徒。
佛法,真地无边?法师的唇角突然颤抖,雪花飘落,将他的眉宇染成雪一样的颜色。他移动着自己的身躯,如同千斤之躯,缓慢而且沉重,他仿佛突然之间被人点中死穴,脸色煞白,喃喃自语:难道,佛法真地无边?
我被眼前的情形惊呆,忘记拂落肩上的雪花,任凭它一片片飘零,如同夏季的樱花,美丽但却冷酷。师傅走到我的面前,我安静的注视着他,原地不动。仿佛两尊佛像,一尊等待另一尊的答案,而答案又会是怎样的结果呢?
师傅……许久之后,我克制不住的轻声呼喊,我无法继续冷静地看着师傅面容憔悴的难过。
是啊,难道,佛法真的无边?师傅的脸色开始恢复正常,说,周建,为什么,身处佛法的笼罩之下你却会提出如此的质疑呢?难道,十一年修行只是让你在今天,在你十七岁的冬天当面质问你年老的师傅,问他,佛法真的无边吗?
法师激动的脸孔有些赤红,站在山的顶端,他泪眼婆娑,我理解他的感受,作为几十年的信徒,师傅也只是耐心地遵循着佛的旨意去教化自己,以及我,和现在或将来所有相信佛的信徒,他似乎没有想过,也不用去想,在他年老,在他因为佛法精妙而成为人人推崇的一代名师时,他曾预言过今生与佛有缘的门人会毫不犹豫地质问他佛法是否真的无边。
然而,这却是最难得可贵的,法师的表情突然变得十分喜悦,他轻轻地拂落眉间的雪花,对于佛法,怀疑才是通往佛法真谛的唯一途径,当你对自己的信仰产生怀疑,你才有继续探究的动力,而不只是一味的困扰。
周建,法师缓慢地喘口气,我们都是佛法的追随者,而不是终结者。只有不断历练循环,才是唯一的出路。
周建,法师突然大声呼喊,你看那天……
我仰起头,看着无穷的天际。
你看那天有多高有多宽,佛法就会有多么无边。法师双手高举,大风凌厉地将他的长袍吹得如同撕裂的旗帜,仿佛有一股风从他的脚下升起,将他银白色的胡须满天飞扬,我看到他的神情庄重而且严肃。
我目瞪口呆地望着眼前的老人,一时间我无法完全领会法师的答案,只是默不出声地站立,法师转过身,似乎想要离开。
周建,也许是你该离开的时候了,法师没有回头,沉缓地说,他突然停住身子,说,周建,今生你注定与佛有缘。
(第一章完)

- 服务号
- 朋友圈





 官方微信
官方微信 官方QQ
官方QQ
 官方博客
官方博客 官方直播
官方直播
 官方美篇
官方美篇
 在线礼佛
在线礼佛